登录35斗
三农专家温铁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未来农业的内涵
9月20日至21日,2023未来农业产业大会在陕西杨凌成功举办。大会邀请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温铁军,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其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继芳,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姜道宏等院士专家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其中,“三农专家”温铁军报告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未来农业的内涵》,现分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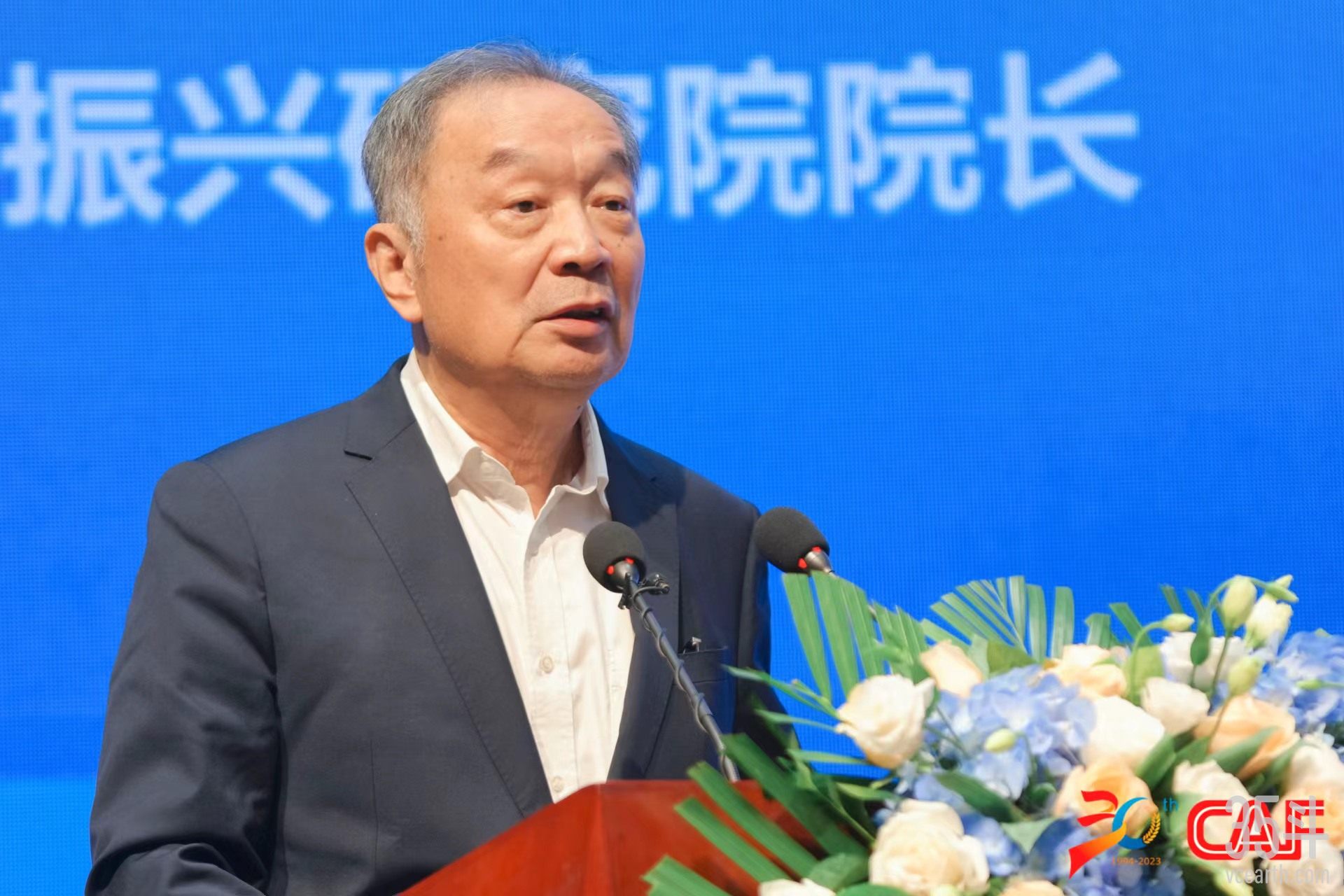
温铁军,男,1951年5月生于北京,管理学博士、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疆大学“天山学者”、海口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粮食安全专家委员、国家发改委新型城镇化专家委员、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专家委员,商务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市、重庆市、福建省等专家顾问,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董事。
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等职,先后担任过多个国家级项目首席专家。
我长期专注的领域是政策研究,所以对于未来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会更多地关注。农业与14亿人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直接相关,这些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农业劳动力中的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失有直接关系。按照现在的统计局统计的指标规范,凡在城市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的就算城市人口,这个比重已经高达66%,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生活在农村。
同时,由于城市工业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优质劳动力,所以农村向城市贡献的劳动力资源也主要是青年劳动力,也就是黄金劳动年龄段贡献给城市,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养老、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其实是甩给了剩余过少的农村。所以长期以来,当我们讲农业的未来,讲到提高农业的装备系数,讲到提高农业的信息化程度、科学化程度等等这些的时候,对应的主体恰恰是草根。
也因此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广的覆盖面,恐怕就有很大的缺陷。对“草尖”18-30岁的劳动力,推广技术的成本是低的;对40岁、50岁以上的“草根”劳动力,技术推广的成本是高的。客观上我们看到农业未来需要科技发展,需要有很多技术推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不调整现在的政策,继续沿着旧阶段,单纯地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当成是中国现代化主要内容,那我们恐怕很难把现在已经形成的技术发展成果,真正应用到乡土社会只剩下草根劳动力的领域之中,所以希望大家适当关注。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自确立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以来,所明确提出的现代化内容。它针对的一是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二是什么才是精神文明。我们五大特征中的第三个特征叫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什么才是真正符合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要求的精神文明?这和我们现在的教学、科研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包括技术创新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希望愿意考虑。

这些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求的技术,一定程度上具有“去生态”甚至“反生态”的特征。
我们都应该知道,工业是一个资本增益排斥劳动的客观的内在机制体现过程,而城市化是资本高度向城市集中,但同时也是风险高度向城市集中。从经济学研究角度来说,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它们是同步的。所以当我们追求“工业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这种发展方式的时候,其内在的“反生态”特征,是伴随着资本和风险高度集中而同步发生的。因此我们以往这一百多年来无论哪一个朝代和党派追求的都是“工业化+城市化”,客观上对资源禀赋非常差的国家、人口规模巨大的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就不是简单的正面的,而是应该看到所形成的代价是巨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十六大以后就开始明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强调加强新农村建设,试图改除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方式,但由于这个阶段我们深度融入全球化,极大程度地受到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资本投资的左右,而使得定下的发展方针不可能非常顺畅地推行,实际上形成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个阶段因为“草尖”劳动力流出,留下的是“草根”,农业不能再用过去的劳动力方式来从事传统农业的经营,因此也在被工业化改造,实际上就导致了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八大开始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基础,并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跟乡村振兴是同步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也要求着,我们从事科学技术的这些研究人员应该考虑,怎么把生态化建设——也就是二十大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四大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成是科研的方向,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前一个阶段所形成的这些问题。
所以越是激进主义,越是消费主义,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这一点科学技术至少不应该追随激进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趋势,而是要改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上来。
这些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即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设施型资产。
我们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以实体资产为底座,金融资产和债务资产相对占比并不那么高的发展结构,我们还有大量的实体型资产是可以被启动起来,它现在处于沉淀状态。我们跟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相比,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实体资产占比过低,所以对中国来说,只要我们进入现代领导人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把我们的发展重点放在如何启动国内已经客观形成的大规模实体资产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在这条不同的道路的指导思想上,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了农业发展新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大食物观”,用以替代狭义的农业安全观。
当我们讲到粮食不足的时候,从结构分析来看,其实粮食进口的超20%份额中,绝大分布是饲料粮、油料粮,而不是主食粮。如果看主食粮,看食物总消费量,从1978年每人515千克增长到现在1400千克;而人均原粮消费量从1978年每人每年247.8公斤到130公斤,是大幅下降的,所以现在粮食安全概念也正在调整,把它变成主粮,主要是食用这一部分的安全观,因此不是主食用粮的短缺,主要是其他消费,特别是饲料消费。再进一步看,其他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人均健康所需要的消费,比如城市人口中肥胖率大幅度上升,与“农业需要和健康结合”这一观点也不那么一致。
所以各位应该注意,农业的结构性变化实际上已经发生,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农业安全观应该是有变化的,现在领导人提出的是“大食物体系”、“大食物观”和“大食物安全”,它就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它就要求“实事求是”,“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从这些方面看,农业发展的新的方向应该是生态化的多元性。未来农业应该朝着多元农业、大食物体系的方向去发展。
在这些要求之下,我们看向欧洲经验。大家也需要了解到,欧洲是在战后工业过剩的条件下,大量的人口转向乡村,农业的经营主体60%以上是市民,市民的绿色主义消费倾向带动了欧洲农业的转型,因此消费对象——我们农口的朋友,特别是搞科技的,我们很少关注,你的目标客户群——即农业这样发展,其对应的消费者,到底是谁?
这里给到一些基本资料:中国引领绿色农业消费的主要是中等收入群体,世界上普遍的概念是中产阶级,这和欧洲的趋势有一比。因此我们可借鉴的模式应该是“莱茵模式”,而不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典型的大农机、大农场的发展模式。而欧洲的“莱茵模式”的很多经验在目前农口的高校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就我们周边来说还有东亚模式,就是“日韩台模式”,即“日韩+中国台湾”这个模式。更主要的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把第三产业中最能够创造增加值的金融、保险、购销、房地产等等,全部装在综合农协这个体系当中,它才有农民收入高于城市收入的客观结果。所以我们到底走哪条路?到底走哪一种组织制度的建设方式,走哪一个方向?这仍然也是值得我们在未来农业发展中认真讨论的。

现在领导同志强调的、和我们未来农业发展组织方式有关的,就是和乡村振兴同步提出的“新型县域经济”。我们要求的是,以县域为单位,来形成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空间资源开发,这也是因为“两山”(编者注: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在新的发展中是指导思想。
“两山”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是山水田林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它不可以被分割,因此要“三全”,必须是“三全”才能体现“两山”开发原则。
“三全”的主要地域关系应该体现在县域,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新的制度建设,应该按照“两山”思想作为指导,体现“三全”开发。当然也就要求科学技术路线和“三全”开发有一定程度的结合。如上文所说,真正的农业第三产业创造增加值,主要是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加工等领域,这些领域应该在县域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闭环,这样才有可能让农村经济,特别是让农民得到长期的财产型收入,我们农业农村才能稳定。农民长期收入有所保障,农业农村发展才能稳定。
对未来农业农村是什么样?恐怕得是“六产结合”。我们提出除了一二三产融合之外,还要考虑健康、康养为代表的“生命产业”等相结合的,我们称之为“农业六产化”(编者注:包括农业、工业、旅游业、自然教育、生命产业、历史传承)。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进一步发展的就是新型县域经济中的新型市场经济建设。
注:文中如果涉及35斗记者采访的数据,均由受访者提供并确认。
声明:35斗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35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转载请联系gao.kp@vcbeat.net。
用户
反馈





